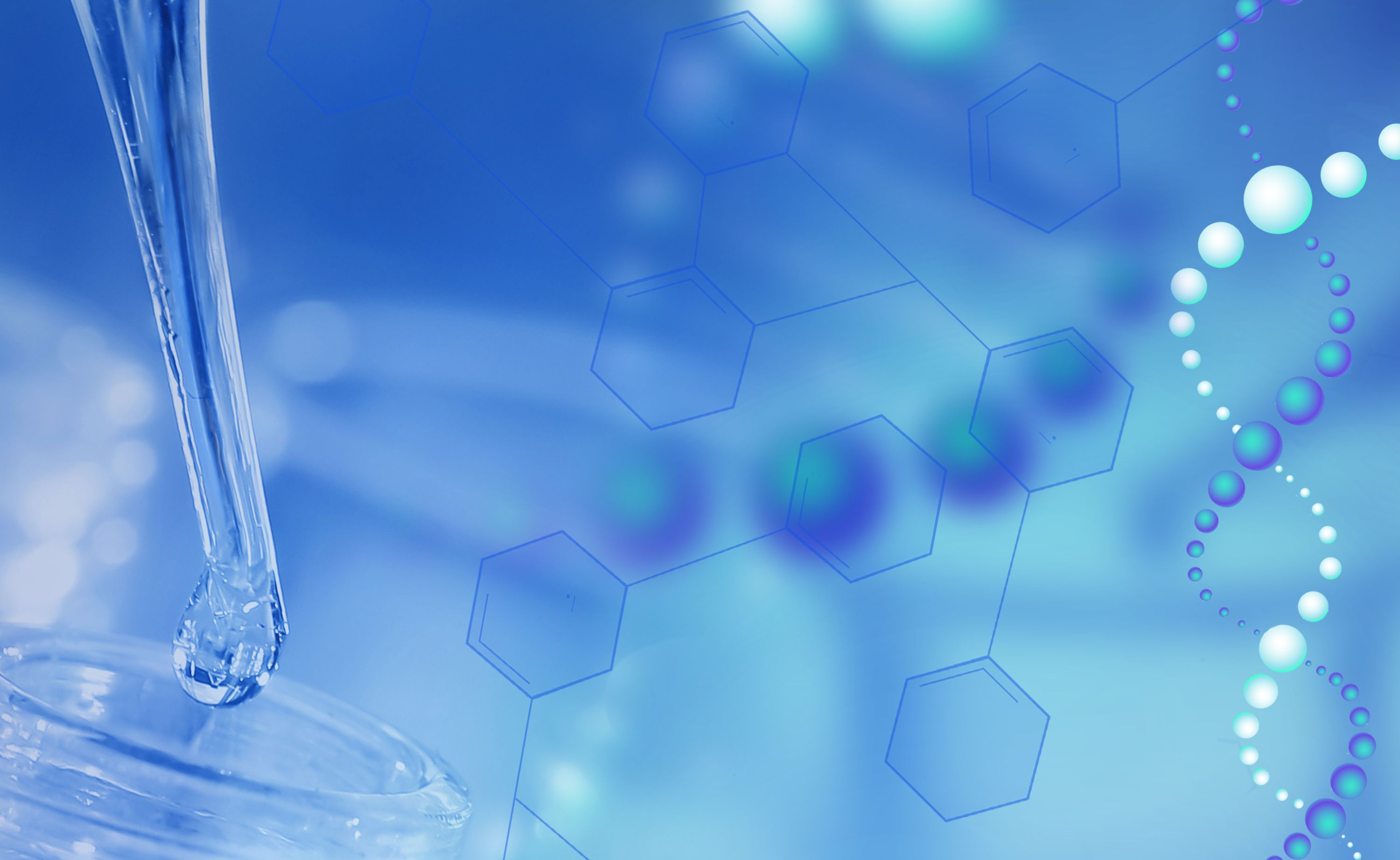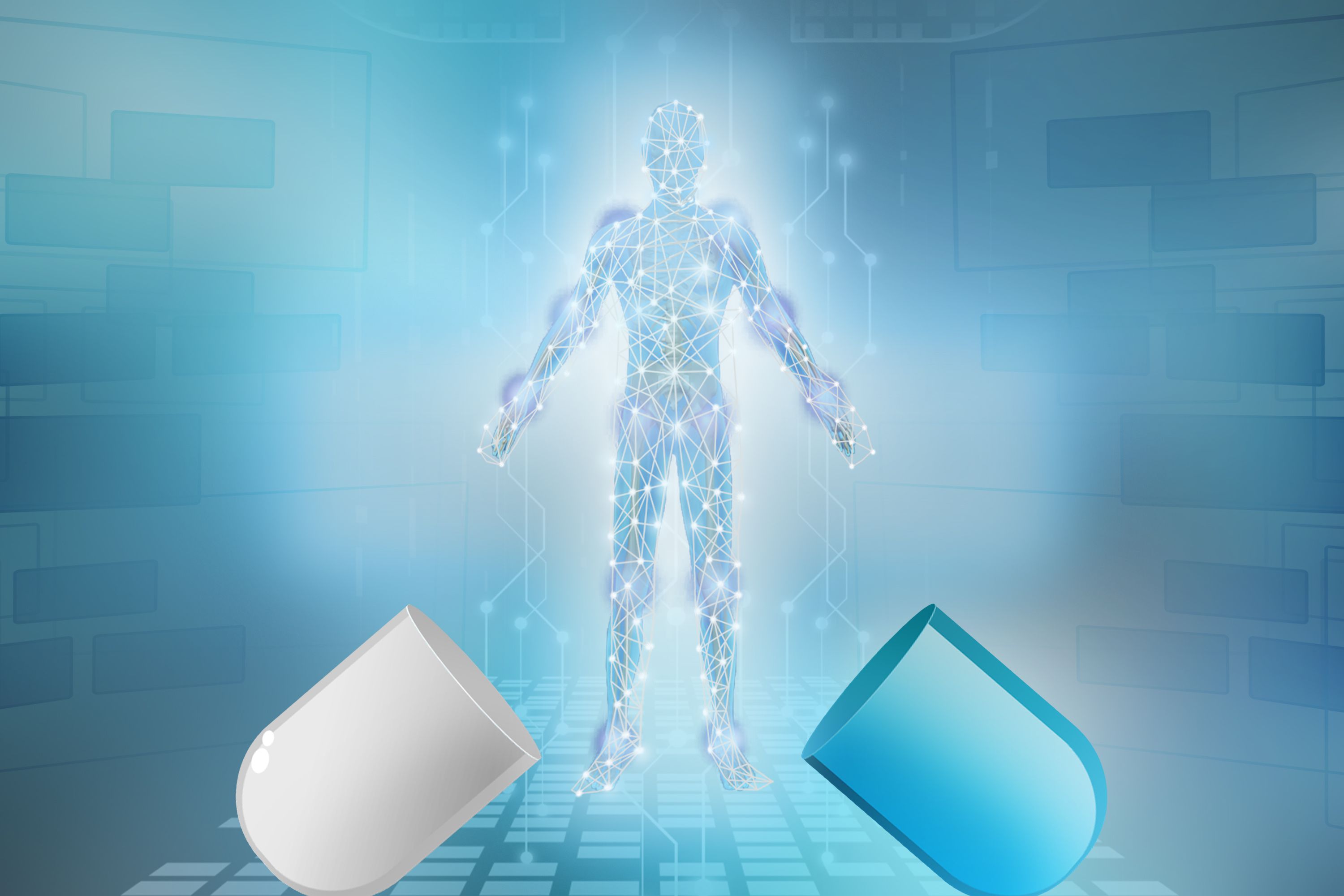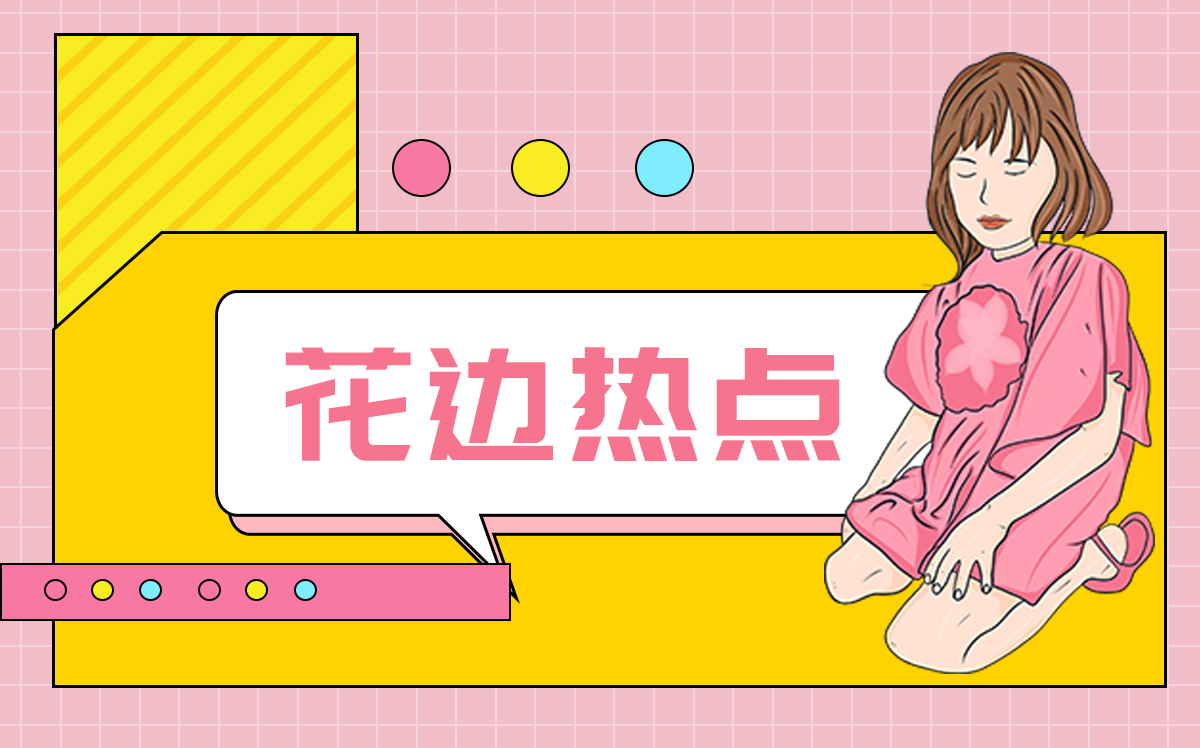(资料图)
(资料图)
原标题:秦汉小学字书的历史沿革与文化精神
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识字教育与“书同文”的传统,先秦两汉的小学字书正是这一传统的产物。小学本为初等教育之称,因其以识字与“六书”为主要教学内容,故汉人亦称文字学为小学。历史上最早的字书当为西周中晚期的《史籀篇》,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所作,以大篆书写,为四言韵语,共十五篇。黄德宽、陈秉新先生指出,周秦时期至少有两次汉字整理活动,第一次发生在西周中晚期到春秋之际,第二次发生在秦始皇时。《史籀篇》是第一次“书同文”的产物,而在第二次大规模的“书同文”运动中,更出现了对秦汉小学影响深远的《苍颉篇》。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详细梳理了秦汉字书的历史沿革。李斯以小篆统一文字,作《苍颉篇》七章,赵高作《爰历篇》六章,太史令胡母敬(《说文叙》作毋)作《博学篇》七章,皆以小篆书写,作为秦朝统一文字的样本。到了汉初,“闾里书师”将《苍颉》《爰历》《博学》三篇合并,作为当时的识字读本,统称《苍颉篇》。秦代的《苍颉篇》以小篆书写,新成的三合一版本亦当为小篆,这是《说文》小篆字形的基础来源。与此同时,目前所见的出土《苍颉篇》残简皆为隶书,说明它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“隶化”转写。汉代的《苍颉篇》四字为句,隔句押韵,以六十字为一章,凡五十五章,共3300字,其中略有重复之字。秦汉以来,汉字大量分化造字,字书的收字范围亦不断拓展。汉武帝时,司马相如作《凡将篇》,对《苍颉篇》的收字加以增补,没有重复之字。此外,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《急就篇》,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《元尚篇》,则皆未超出《苍颉篇》的收字范围。到了汉平帝元始年间,在王莽、刘歆的推动下,西汉王朝组织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文字征集、整理工作,上百名“通小学者”会集长安,研讨文字,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文字学大会。在广搜字形、字说的基础上,扬雄作《训纂篇》,凡八十九章,将《苍颉篇》扩展为不重复的5340字。东汉以后,班固在《训纂篇》的基础上增续十三章,添加780字,共一百零二章,6120字,自谓“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”。此后贾鲂作《滂喜篇》,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将其与《苍颉篇》《训纂篇》合称为“三苍”。根据段玉裁的统计,《滂喜篇》把两汉字书的收字增加到7380字。在前代字书的基础上,许慎“博采通人,至于小大”,进一步搜集不同来源、不同时期的汉字形体,对其进行缜密的优选和“篆化”处理,将《说文》收字拓展为正篆9353字(今本正篆为9431字),分析字形、说解字意、标识字音,以部首为枢纽建立起体大思精的汉字体系,成为秦汉字书的集大成者。
秦汉字书的规模不断扩展,从《苍颉篇》到《说文解字》拓展了将近三倍,反映出先秦两汉不断分化造字的汉字史规律。其纂集方式也由韵文短句的识字读本,发展为统摄汉字形音义体系的“小学”专著。这一历史性的跨越,与秦汉文字规范的核心理念密不可分,更受到秦汉经学的深刻影响,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。
秦汉字书是“书同文”政策的产物,其核心理念在于规范与秩序。“规范”体现为汉字的形义统一,这与先秦以来的正名思想密切相关。以《苍颉篇》为例,其篆文虽已不存,但泰山、琅琊等地的秦刻石中仍有秦篆遗存。战国时期文字异形,汉字的理据与字用颇为混乱,秦篆则是形义高度统一的文字体系。整体而言,秦篆固定了偏旁的写法,确定了偏旁的位置,废除了异体异构,统一了书写笔画,实现了构形系统的完善和个体字符的优化。《苍颉篇》是秦汉小学的开端之作,它保存的小篆字系的构形规律及其选取字形的标准,对两汉小学、特别是对《说文》具有根本影响。“秩序”体现为对汉字体系的整理,早期字书的编纂中蕴含着部首的滥觞,展现出对汉字系统的朴素认识。在《苍颉篇》中,已将意义相近、相关的汉字编排到一处,如北大简《苍颉篇》将从“木”的“松柏橎棫,桐梓杜杨,鬱棣桃李,棗杏榆桑”集中排列,其中虽掺杂了“鬱”“棗”等字,仍能体现部首归字法的滥觞。到了史游的《急就篇》,汉字的分类观念更为成熟。他明确提出“分别部居不杂厕”,意味着自觉的类聚意识,开《说文叙》“分别部居,不相杂厕”之先河。《急就篇》以物类划分汉字,由于汉字形义统一,同类之物多同部首,因此出现了将同部字归属于部首之下的编排方式。如“稟食县官带金银”一句,在“金”字之后列“银、铁、锥、釜、锻、铸”等33字。在整齐的物类划分中,以部首类聚汉字的新模式已经跃然欲出了。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言,“是编不可没之功,尤在分别部居,实开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分部系字之先”。可以说,在规范与秩序的理念下,秦汉字书不仅具有识字教育的功能,更开启了自身的学理化之路,奠定了传统“小学”注重形义统一、追求系统条理的学术特点。
秦汉小学更与两汉经学息息相关。一般认为小学源自古文经学,事实上,二者的关系更为复杂,经历了“同源—独立—合流”的过程。小学与古文经学皆源自先秦儒家,其中的关键人物是荀子。小学是“书同文”的产物,李斯为荀卿弟子,其文字规范思想颇受荀子思想之影响。与此同时,荀子又是古文经学的先师,《毛诗》《左传》皆为其所传。尽管二者可以追溯到同一源头,但早期小学实有其脉络渊源。无论是司马相如、史游、李长、爰礼、扬雄,其人皆不在经学传承之中。西汉小学家多能作赋,相如、扬雄都是辞赋大家——想要“铺采摛文,体物写志”,必须先要掌握大量汉字。西汉经学家则鲜有作赋之事,这恐怕不是经生不屑于文章雕虫,而是因为其识字有限、难于铺陈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记载,汉武帝曾令李延年为协律都尉,让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诗赋。《史记·乐书》曰:“至今上即位,作十九章,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,拜为协律都尉。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,皆集会五经家,相与共讲习读之,乃能通知其意,多尔雅之文。”《史记》中的“十九章”即《汉书》之“诗赋”,相如作赋,用辞博洽,需要汇集五经博士才能通读,足见小学家与经师的学风差异。西汉中期以降,小学逐渐与古文经学合流,这与后者“通经博览”的学术特点密不可分。汉宣帝时,张敞以古文家受《苍颉》之学,当为古文经学吸收小学之始。汉平帝时,刘歆借助王莽的政治势力推行古文经学,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经学运动,其中即包括“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,各令记字于庭中”的盛况,亦体现出二者的合流趋势。到了东汉,小学与古文经学的融合日趋紧密,东汉古文家如桑钦、杜林、卫宏、徐巡、贾逵等人多兼通小学,其字说也多为《说文》所征引。东汉古文家对“六书”展开了深入探讨,现存班固、郑众、许慎三家的“六书”之说,皆为古文经学。与此同时,东汉古文家多善作赋,张衡、班固、马融皆有传世之作,与西汉经师罕能作赋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凡此种种,正如卢植上书所言,“古文科斗,近于为实,而厌抑流俗,降在小学”,二者已融合无间。正因如此,小学不是单纯的识字之学,而是贯通了汉字与汉语、汉字与经典解释,成为了经学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总而言之,秦汉字书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,更是秦汉思想学术大背景中的产物。《说文叙》说:“盖文字者,经义之本,王政之始。”作为秦汉字书的高峰,《说文》代表了秦汉字书的文化精神。一方面,“书同文”是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基础,在字书中也蕴含着秦汉古人建立体系、囊括万物的雄大气魄。一方面,汉字具有因形求义的功能,其所携带的语言、文化信息是阐释经义的重要参照,字书指向了浩瀚的经典世界。在“王政”与“经义”的整体视域中理解秦汉字书,我们看到,它基于识字读本而又超越了识字读本,最终形成了以《说文》为代表的人文经典,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成。
(作者:孟琢,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、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副教授)